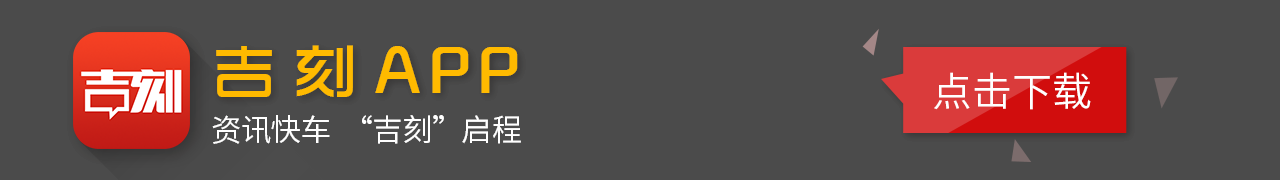王欣睿
内容提要:“闯关东”作为一种独特而典型的东北文化表意系统,早已成为众多学科的公共研究场域和被普遍认同的概念。而中国文学研究界对“闯关东”题材作品的关注则非常薄弱。本文从“闯关东文学”命名的合理性及必要性出发,首次提出并阐释“闯关东文学”概念,梳理“闯关东文学”的历史流脉,解读“闯关东文学”作品的史传叙事风格及展现东北生活画卷的艺术特色,最后探寻“闯关东精神”及其价值意义。
关键词:闯关东 闯关东文学 闯关东精神 历史价值
“闯关东”作为以中国东北地区为目的地的人口迁徙活动,构成了中国近代移民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迁徙人数最多的移民潮。这一移民潮在迁徙语境、迁徙方式和迁徙功效等方面既具有中国近代移民史的典型面相,又有许多独特之处,其过程与结果对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刻影响。不过遗憾的是,在中国文学界还没有专门的“闯关东文学”研究。然而,以“闯关东”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数量却相当可观,据笔者初步统计,相关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和民间故事等文学作品有200余篇。但是,中国文学研究界对此的关注却相当薄弱,甚至连“闯关东文学”这一可能与“大墙文学”、“北大荒文学”等相提并论的概念都没有正式出现,叙述这一浩大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的文学创作似乎成为被遗忘的角落,湮没在各时期文学史的主流叙事之下。
一 何为“闯关东文学”
何为“闯关东文学”?这是一个首先必须厘清的文学史概念。与相对清晰的“闯关东”概念本身不同,“闯关东文学”是一个比较模糊和笼统的概念。具体说来,包括广义概念与狭义概念两个层次。就狭义概念来说,就是指描写“闯关东”历史、讲述“闯关东”故事、叙事作品中以具有“闯关东”经历的人物为主角、具有东北地域特色的文学作品;而就广义概念来说,是指具有某些“闯关东”历史元素的文学作品,这些元素可以是作品中一个人物的经历,也可以是以“闯关东”作为一段情节的背景。
“闯关东文学”命名是从题材角度出发考量的。它是实践性文学,是伴随移民历史潮的发生发展孕育而生的,但“闯关东文学”创作并未因“闯关东”移民的结束而终结。此类文学作品的体裁多样、内涵丰富,通过移民或他者的视角关注了东北历史的发展进程。我们从作品中能观感到“闯关东”移民潮的数量、移民来源、移民路线、移民选择的职业等方面的复杂性,东北民俗的丰富性,东北文化的包容性及东北历史的变化性,等等。可以说,“闯关东文学”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我们可以从文学视域下感受到移民潮带给东北的深远影响及东北的发展价值理念。所以,以题材意义命名“闯关东文学”是有其合理性的。
伴随电视剧《闯关东》三部曲的热映,“闯关东”移民现象再次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闯关东”相关研究及评论文章快速生产,进而以“闯关东”作为写作背景和主体内容的小说、报告文学、人物传记、散文、诗歌及民间故事被重新打捞和翻检。“闯关东”的经历者及其后辈,因那段悲壮的迁徙史而感动的作家,纷纷以文学的方式找寻那段历史,以文学的视角关注那段历史,对闯关东历史的关注甚至激起一些作家心中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可以说,“闯关东文学”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被重新激活,对其的整理和研究也日益变得势在必行。而在此我们必须首先明确的一点就是,“闯关东文学”绝非这些年才创生的新现象、新门类,它的历史很长,滥觞于清朝,绵亘20世纪。
二 “闯关东文学”的历史脉络
梳理“闯关东文学”的历史脉络,首先应该理顺“闯关东”移民潮的历史。“闯关东”并非是中国近代东北历史上的突发现象和偶然事件,其生成和发展有着清晰的脉络和完整的过程:从1651年到1949年,历经了清朝顺治年间的招垦,康熙乾隆时期的封禁,咸丰光绪时期的解禁,以及民国初期的“大移民”和伪满洲国时期“抓劳工”等多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与发展过程。“闯关东”大潮横跨300多年的历史时间和多种社会阶段,先后有3000多万来自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地民众因战争纷扰、匪患肆虐、灾害频发、赋税盘剥等原因背井离乡,冲破“柳条边”,奔赴东北开疆扩土,投身耕作、挖参、淘金、放排、经商、采矿等行当,最终构成了“闯关东”这一宏大的历史移民浪潮和庞大的“闯关东”群体。“闯关东”不仅仅是一次单向度的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人口大挪移,更是一次政治、经济、文化意义上的多向度的重构和再生。东北的农业、工业、商业和军事的崛起,都与“闯关东”大潮息息相关,这不仅改变了中国东北及周边国家地区的人口与族群的规模和结构,而且重新划定和确认了东北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位置。尤为重要的是,经过文化交融和发展,“闯关东”已经从外在的人口迁移逐渐演化为内在的精神根基,九死一生“闯关东”所衍生出来的蛮野力量、英雄气质、冒险精神、侠义品格、暴力崇拜和乐观态度等一系列文化性格,构成了东北文化和东北人独特的内在气韵和性格品行,进而形成了独特而复杂的“闯关东精神”。这种思想性格不仅改变了历史上东北社会的进程,而且深深地影响了当下东北社会的发展和态势。
需要指出的是,就“闯关东”历史事件本身,本文所限定的时间终点是1949年。虽说此后仍有政府组织或鼓励的集体性与个体性“支边”以及各种自发的个体性迁徙行为,但都与过去的“闯关东”有了明显的性质差异。因此,对于以此时段外来人口迁徙到东北的故事为主要题材的创作在本文中暂不涉及。
“闯关东文学”有着十分清晰的发展脉络和时间框架,其与“闯关东”移民现象同步发展并延伸至今,可以将其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清朝初年到清末时期(1651年至1911年),为“闯关东文学”的最初发生期。从近现代中国文学史来看,“闯关东文学”的发端是以纪实类作品为主的民间创作,主要记载“闯关东”移民的足迹及关东风情,体裁大多以历史传说、民间故事和民间歌谣等为主,如人物传说《秃尾巴老李》;地方传说《五台山》;土特产传说《乌拉草的故事》《李连贵熏肉大饼》;还有表现行帮文化中的淘金文化篇,如《金狗》《金洞》《巧得马蹄金》等等;参帮文化篇,如《红参和人参的故事》《孙把头》《老把头救石哥》《王红挖参》《九扣还阳草》等等。这些故事往往不是一个版本,在流传时故事的人物和细节又经不同人的编撰而略有差异,但是表达“闯关东”的故事是相同或相似的。此外,还有一部分“闯关东文学”是不可忽略的,即“流人文学”中描述东北风土民情的文学作品。被清廷流放的“罪臣”和“文人”所写的诗文、笔记等,如杨宾的笔记《柳边纪略》、吴兆骞的诗集《秋笳集》、方式济的笔记《龙沙纪略》等文学表现力更强,生动描述了东北旷达而恶劣的自然风貌、行迹边疆的独特体验。当然,严格意义上说,“流人文学”不属于“闯关东文学”,因为“闯关东文学”中的“闯”的含义本身就是因生活所迫一种大胆、冒险的“主动”行为,而“流人文学”则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被动地进入关东。不过,“流人文学”也给后来的“闯关东文学”提供了独特的文学资源与情理先声,因此我们在此把这类文学作品也视为“闯关东文学”发生期的现象之一。
第二阶段是民国时期(1911年至1949年),为“闯关东文学”的发展期,这时期的“闯关东文学”以小说为主。内容上,有些作品讲述了“闯关东”行进路上的艰险与磨难,煎熬与拷问,如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梁丁山的长篇叙事诗《拓荒者》;有记述移民“闯关东”后在东北的境遇,尤其是从事诸如淘金、伐木、挖参、放排等特殊职业的困顿生活,从中可以感受到流淌在他们笔尖上的思乡情愫,如骆宾基的短篇小说《乡亲——康天刚》《红玻璃的故事》,小松的短篇小说《部落民》;有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等背景下“闯关东”移民者的凄惨生活及为保家卫国而奋勇抗争的斗争史,如骆宾基的长篇小说《幼年》,渗透着亡国奴的悲怆、民族共融的复杂情感。
第三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1949年至1978年),这个时期是“闯关东文学”发展的过渡期。这时期的“闯关东文学”以“家史”、“村史”等形式的报告文学为主,主旨是“忆苦思甜”,其作品普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突出鲜明的“阶级斗争”色彩,表达的是“闯关东”移民苦难的血泪史。如忆苦思甜的报告文学类《闯关东的那一辈人》《含泪闯关东》《两次下关东的遭遇》等;描写在“闯关东”经历下成长起来的英雄形象,如《林海雪原》的杨子荣,《高加索的烽火》的季寿山等;还有展现“闯关东”现实处境的叙事诗《双塔记》等等。这些作品都从不同角度述说着“闯关东”移民无奈与艰辛的遭遇,谋生与生存的不同道路选择,表现地方恶势力盘剥与欺诈下“闯关东”强烈的求生意识。因此,在指向明确的政治话语之外,也可以看到作为底层民众基本诉求的“活着”。
第四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1978年至2000年),为“闯关东文学”的再次发展期。这时期的“闯关东文学”紧跟“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步伐,由政治诉求向人生艺术发展,文学、文化沿着自身的轨迹嬗变。作品体裁以回忆录、传记和小说为主,兼有散文、诗歌、歌谣等形式,多元化地展现“闯关东”移民的内在情感、个人奋斗史及商号、家族史等内容。从创作和传播过程来看,具有了某些市场运作的因素。文学创作上,以个性化视角切入,多维展示人们的精神风貌,对人性力量给予深度探索,并不断探索叙事疆域,摆脱此前极“左”思潮造成的束缚。代表性作品有展现鲜为人知的关东生活画卷的评书《关东姑娘》等;记载“闯关东”及亡国奴岁月生命体验的回忆录、人物传记《一户侯说》《童芷苓》等;记述历史人物“闯关东”的成长艰辛与发迹史的作品《黄金王国的兴衰韩边外祖孙四代纪实》《张宗昌全传》《响马营长总司令·王德林传》《孙越崎传》等;描写“闯关东”移民人物形象的小说《闯关东的汉子》等。同时,世代流传及实地调研创作的民间文学如诗歌、歌谣、民间故事等等也被陆续出版。
第五阶段是新世纪以来(2000年至今),为“闯关东文学”创作阶段的高潮期。这一时期的“闯关东文学”以长篇小说为主,兼有传记、影视文学和评书等多种形式。“闯关东文学”不仅作品数量增多,而且艺术形式更加多样,艺术质量普遍提高,特别是影视类作品数量剧增,在市场化的系统运作下影响巨大。这一时期的“闯关东文学”在内容上普遍注重表现极端境遇中的人性、人对历史的担当,以及表现“闯关东”这一惊世壮举的文化内涵,如小说《闯关东》三部曲、《东北生死场》、《生死柳条边》等;另外,还有表现东北旧俗“拉帮套”生活的小说《闯关东的女人》、描写“闯关东”移民另类形象的小说《逝去的海南丢》、叙写关东奇异风情的小说《黄金老虎》《狼王》、展现闯关东群体抗日斗争历史的小说《血洗征尘》《战争回忆》等等。
三“闯关东文学”的艺术特色
(一)创业于沃土与艰困之中的史传叙事
“闯关东文学”作品承传了中国史传叙事的传统,在移民潮历史大背景下,运用虚实叙事的艺术手法,绘写着移民的迁徙史。这种创作方式是写作者有意识运用的,这种意识贯穿于情节的架构、故事的延展、人物的设定之中,用恢弘多彩的意态进行展开和描摹。同时,基于历史背景下的传奇故事也具有文学意义与时代意义,是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趣。“史传叙事”风格普遍化的根源在于“闯关东”历史自身携带的“创业”质素,“创业”本来就是各民族史诗的最早主题之一。而“闯关东文学”中的“创业”本身就包含着两面性:
一方面,东北地域空旷的沃土带给这些山东、河北等地的农民、流民以生存的希望,有开天辟地般的豪情。诚然,“创业”最大动力是移民动因,从移民学的角度,这次移民潮既有迁出地的“推力”,即迁出地的自然灾害频发、税赋严重、人口压力巨大、土地矛盾激化等原因;也有迁入地的“拉力”,即迁入地土地肥沃、清政府解除禁忌的政策、土地政策相对宽松等原因。无法生存下去的底层百姓、没有或仅有微薄财产和土地的流民便游走他乡。这些移民者主要来自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尽管北方气候条件恶劣,但中原底层农民冒着种种风险走过的“闯关东”的艰辛旅途,是悲壮的求生路,“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①。
“闯关东文学”算不上是严格意义的历史题材,但它较为真实地记录了移民者勇闯东北的足迹。现实中,尽管东北严寒天气让人畏惧,“山东老家的天也冷,可那个冷冻的是皮肉,而关东的冷冻的是骨头,冻的是五脏六腑”②,但传说中的东北“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吃不完的手把肉,喝不完的大碗酒”③也让人充满了生存的期许,“它吸引着一辈辈风云人物来到这里披荆斩棘,断草开荒,求生息繁衍”④。“闯关东文学”的创作就是在展现移民地风貌及移民者真实境遇的同时,感受“创业”的力量和人们的热情,史传叙事可谓恰如其分。
另一方面,移民者离开熟悉的人际网络,完全要靠机智和武力,甚至是运气和周围环境打交道、争生存,东北地区又有土匪、俄国人、日本人的暴虐,每一天都充满了不确定和挑战。“闯关东文学”中故事的曲折传奇与跌宕起伏就呈现了每位想逃离故土的移民者的“闯关东梦”。这些内容中不仅仅展现了关东生活的淘金业、农业、商业、矿业图像,而且对于东北的行帮业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如匪帮、山帮、参帮、放排帮、妓女帮的规矩、特征等,还有关东大地上满人、汉人、日本人、朝鲜人的不同精神状态。
“闯关东”这段历史内涵丰富,有民俗、有故事、有文化、有精神,以文学来表现的难度之一就是如何处理好历史与虚构的关系。作家大多以真实的历史为平台,搭建起历史大事件下不同层面的虚构故事,描绘了“移民潮”景观,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文学“史传传统”的尊重和继承,在对人物性格和具体情节的处理上通过丰富的想象而表现出了非凡的传奇性。
(二)繁衍于沃土与礼俗之间的生活画卷
“闯关东文学”的审美性一方面表现为用文字描述东北酷寒与荒蛮地域风貌的奇特;另一方面表现为东北土著部落民风民俗怪异,还有“闯关东”移民者踏足东北后面对礼俗断裂的困顿与纠葛,道德伦理的冲突与挣脱……东北地域“生活画卷”共生了“闯关东文学”的审美特色。
东北地处祖国的边疆,是寒温带气候,冬季漫长、寒冷且干燥,尤其是黑龙江一些地方还有永久性冻土,荒寒的地理条件必然会形成居民某种特殊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性和民俗。东北各种民俗体现在东北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而这些日常生活在东北文化中就是一种具有独特美学特征的世俗景观。如“闯关东”移民潮初期,描写有关东北冰寒风貌的文字是流人被流放在关东时所创作的诗歌和纪文。在流人心中,繁茂的中原与萧寂的边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情感的冲突也使他们笔下的文字显得尤为深刻:“树木不生,鸟兽绝迹,悲风昼夜呼号,飞沙朝夕霾雾。饮惟酪,食惟膻,毳幕荒凉,孤身寥寂,冰山雪窖,酷冷奇寒。”⑤
东北部落民俗文化指的是东北地域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民间风俗和生活文化,表现在东北少数民族的服饰、居住建筑、饮食文化、民间艺术、礼节、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在“闯关东文学”作品中就展现了众多关于东北习俗、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图景,如“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烟袋”、“养活孩子吊起来”等关东十八怪的说法,这是关东人多年的生活经验的结晶。
“闯关东”移民入乡随俗,学习并保留了大部分应该在寒冷地域及野兽出没地生存的良好习惯,如服饰上关东三宝“人参、貂皮、靰鞡草”的穿戴;饮食上多以酒肉为主的风格;房屋设计上多采用泥、砖垒砌的火炕等等民俗观无不表现出关东人民的智慧,使我们加深了对东北人和东北文化的认识。不过,东北见怪不怪的民俗大部分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悄然淡出历史舞台。“闯关东”移民大部分来自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山东,来自礼俗繁缛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但艰难的环境逼迫着移民者打破他们繁缛的礼俗,从“礼俗的困境”突围以保证生存,而挣脱礼俗后的“反弹”,甚至“性解放”到认可“拉帮套”式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也以中原教化为底气革除匈奴族愚昧的“收继婚”⑥民俗等等。在男尊女卑的旧社会中,女人的地位是卑微的,中原地区辈分再高的女人也不能上桌,而且宴请宾客的座次、菜品的摆放都是依礼依规的,否则是失礼的行为。而在人迹罕至的东北,面对一望无际的荒地,人口不是负担,而是最急需的资源。在这里,礼数不受规约,甚至青年女性都成了劳动力、战斗力。这些“闯关东文学”作品里展现的“奇特”民风“生活画卷”也是“闯关东文学”的特色。
四“闯关东文学”的人文精神及审美价值
纵览“闯关东文学”作品,我们透过不同体裁、不同题材的文本叙述,能够发现蕴藏在“闯关东”主题下的一种价值取向、一个不变的呼唤、一种基本理念,这就是“闯关东精神”文化。“闯关东精神”是在“闯关东”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地蜕变与升华,对它的阐释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读。但“闯关东精神”的核心是“闯”,这是一种不安现状的“闯”,一种敢为人先的“闯”,一种不畏险阻的“闯”,一种任劳任怨的“闯”,一种顽强拼搏的“闯”,一种重义守信的“闯”。“闯关东精神”是东北地域文化典型的精神代表,它是交融了原东北游牧文化与中原儒家文化之精神实质,随着东北土地上人们的继承与发展,逐渐演变成为有着现实意义的“闯关东精神”。
“闯关东”对于东北来说是一段重要的历史,这段历史记载了东北人艰苦创业、创建家园的足迹和经历,承载了源自中原的传统文化记忆,也塑造了东北人不惧艰险、百折不挠的性格。“闯关东文学”所展现的迁徙史和移民生存史极具地域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
“闯关东文学”特色鲜明,其对民族文化冲突的展示、对民族性格的表现、对典型东北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其在具有社会和历史价值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闯关东文学”着重表现出了人对“生”的渴望。如在高满堂的《闯关东》三部曲中,移民不畏艰难到东北寻求生计,面对荒芜的土地,“闯关东”移民靠着自己的双手与大自然搏斗,谋求生存。面对艰苦与危险的工作,如淘金、放排、采参等,他们靠着智慧与勇敢,冒着生命的危险为生活打拼。面对战争和动乱,他们挺身而出,奋勇保卫家园,用自己的鲜血捍卫自己的生存空间。进入和平年代,“闯关东”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在“闯关东精神”的照耀下,继续努力奋斗,为了富足而自由的生活而不懈努力。
“闯关东文学”生动地展示了民族的文化精神。“闯关东”文化是生存意识下的历史选择,是民族文化冲突与交融的蜕变。文化的滋养孕育了“闯关东精神”,这是北方民族的魂魄。“清代中晚期开始,随着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区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东北,关内传统的中原文化特别是齐鲁文化对于东北文化的影响也进一步强化。”⑦“闯关东”移民的主体是众多中原的底层民众,他们虽然大多是目不识丁的体力劳动者,并不是精英文化的传承者,但他们在中原大的文化环境的熏染下,行为举止中渗透着中原文化的精神内涵,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风骨,这体现在他们的行为举止、生产方式、道德观念、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
“闯关东精神”是近代东北文化的魂魄,也是当下东北振兴与文化重构的精神资源。在不同的时代里,“闯关东精神”作为一种思想与生命力量,生发出了“东北抗联精神”、“北大荒精神”、“铁人精神”等,成为了东北的重要精神源泉。“闯关东”移民与东北本土的各族儿女一起,无惧自然的荒寒与外敌的残暴,在与自然的抗争和与外敌的战斗中形成了顽强的意志、包容的气度与和谐共生的智慧,这些思想品格和气质共同构成了“闯关东精神”的内核。在东北振兴与社会转型的历史节点,重新发掘、探究、继承和发扬“闯关东精神”,对于东北社会与文化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研究“闯关东精神”,旨在对于祖辈的创业历程表达一种尊敬和纪念,对于新一代人的创业精神给予一种激励和期待。
注释:
①李衡眉:《移民史论集》,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243页。
②③冷言、雪峰:《皇天后土》,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14页。
④何青志:《吉林文学通史》(上),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9页。
⑤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六,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⑥“收继婚”出自《燕赵文化史稿魏晋北朝卷》,陈瑞青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46页。“收继婚俗,史载:‘父兄死,妻后时执嫂:若无执嫂者,则己子以亲之次妻侗叔焉,死则归其故人。’”史载出自《三国志》,卷三十《乌丸传》。
⑦张福贵:《东北文化历史构成的断层性与共生性》,《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7期。
[王欣睿吉林大学文学院邮编130012]